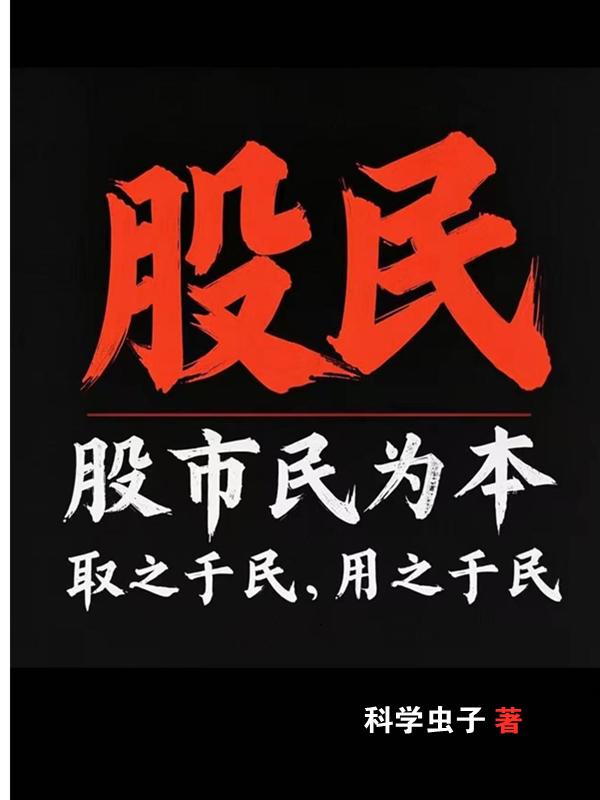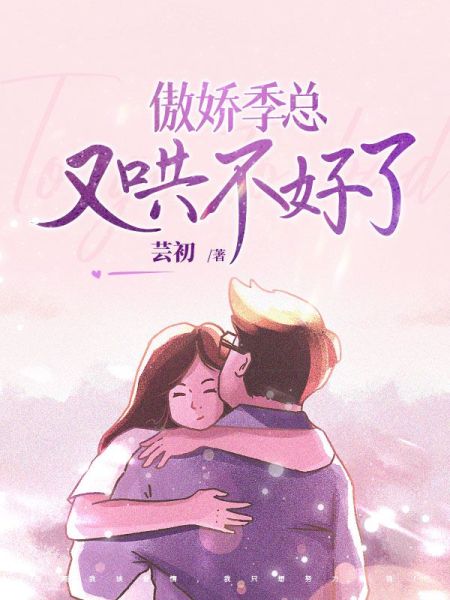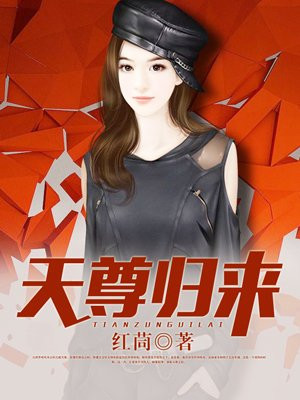第1章 月尘稻
2175年的柏林,春天是带着铁锈味的。
阿明蹲在勃兰登堡门的残垣下,指尖抠进混凝土的裂缝里。风卷着灰黑色的辐射尘掠过去,打在他露出的手腕上,像细小的沙砾在刮擦。他的防护服早就磨破了袖口,露出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青灰色——这是战后幸存者的底色,和周围断壁残垣上凝结的硝烟痕迹差不多。
他在找吃的。准确说,是找任何能塞进嘴里的东西。昨天联合国的空投舱偏离了预定坐标,落在了二十公里外的废墟里,等他和另外几个拾荒者赶过去时,只剩下被野狗啃过的罐头壳。此刻他手里攥着半块生锈的铁片,正一点点撬开压在瓦砾下的金属盒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盒盖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,里面空空如也,只有几粒发霉的饼干渣。阿明骂了句德语里最脏的话,把铁片扔出去,看着它在碎石堆里弹了几下,滚到一根断裂的钢筋旁。
就在这时,他看见了那粒种子。
它混在一堆扭曲的弹壳碎片里,紫黑色,只有指甲盖大小,表面带着细密的纹路,像被谁精心雕刻过。阿明皱了皱眉,伸手把它捏了起来。战后的废墟里什么都有——凝固的血痂、烧熔的芯片、碎掉的骨头,唯独少见这样规整的东西。他放在鼻尖闻了闻,没有火药味,也没有腐臭味,只有一种淡淡的、像是雨后泥土的清腥气。
“那是‘月尘稻’的种子。”
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,带着浓重的口音,像是中文,又夹杂着几个生硬的德语单词。阿明吓了一跳,猛地回头,手里的种子差点掉在地上。
说话的是个老人,背靠着一截断墙坐着,身上的防护服比阿明的更破,肘部和膝盖处露出了里面磨损的保温层。他的左腿裤管空荡荡的,用一根锈迹斑斑的金属管代替,管子底端磨得发亮,显然用了很久。最显眼的是他胸前别着的一枚徽章,圆形,边缘己经锈得不成样子,上面的图案模糊不清,只能勉强看出一半是红色的,另一半是白色的,中间似乎有什么图案被炮火熏成了同一种灰黑色。
阿明握紧了手里的种子,警惕地看着他。战后的柏林,陌生人比辐射更危险。他认得老人的肤色——典型的东亚人,但这说明不了什么。战争打了一百年,军装换了无数种颜色,子弹却从来不管你是什么肤色。
“中国人?”阿明开口,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。他的德语带着柏林口音,英语早就忘得差不多了,只能用这种半生不熟的混合语交流。这是废墟里的通用语言,就像所有人都学会了在饥饿时如何保持沉默。
老人点了点头,挣扎着想要站起来,金属拐杖在地上拄了两下,发出“笃笃”的声响。“赵建国。”他指了指自己,又指了指阿明手里的种子,“月尘稻,从月球来的。”
阿明挑了挑眉。月球,那是课本里的词,是战争打响的地方,是双方互相扔了无数炸弹、最后连渣都不剩的地方。他从没想过,那里还能长出东西。“能吃?”他把种子举起来,对着灰蒙蒙的天空看了看,阳光穿过辐射层,变成了诡异的橘黄色,照在种子上,泛出一层微弱的光泽。
“能长。”赵建国终于站稳了,喘着气,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他解开背后的帆布包,从里面掏出一个裂口的金属盒,盒子里铺着一层黑色的土壤,看起来和废墟里的尘土完全不同,细腻,,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黑。“耐辐射,三个月,就能收。”
阿明盯着那盒土壤,喉咙突然发紧。他想起父亲还在的时候,家里阳台上有个小花盆,种着一株番茄。那是2165年,柏林还没被完全包围,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浇水,看着绿色的果实一点点变红。后来炮弹落下来,花盆碎了,父亲也没了。
“为什么带这个?”阿明问,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他指的是种子,也指这个老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中国人的基地在东边,离柏林废墟有上百公里。
赵建国笑了笑,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,像干涸的河床。“找人。”他说,“找一个...种种子的人。”他的目光越过阿明的肩膀,看向废墟深处,那里曾经是柏林的市中心,如今只剩下一片高低错落的瓦砾,像一座巨大的坟墓。“但现在看来,或许找到了。”
风又吹了过来,这次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。阿明低头看着手心的种子,紫黑色的外壳在他的体温下似乎微微发烫。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,在炮弹声还没那么密集的时候,父亲抱着他,指着窗外的星空说:“等战争结束了,我们就去种一片地,什么都种。”
那时候,他以为父亲在说梦话。但此刻,攥着这粒来自月球的种子,看着老人手里那盒黑色的土壤,阿明忽然觉得,或许有些梦,是值得相信的。